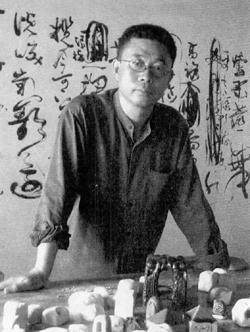 主任,西泠印社理事,国家一级美术师,辽宁省政协委员,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,辽宁省青联常委,锦州市文联副主席,锦州画院院长。全国第五届、六届篆刻展,中国当代篆刻艺术大展、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评委。
主任,西泠印社理事,国家一级美术师,辽宁省政协委员,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,辽宁省青联常委,锦州市文联副主席,锦州画院院长。全国第五届、六届篆刻展,中国当代篆刻艺术大展、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评委。
谷松章(以下简称谷):您的篆刻一直致力于陶瓷印创作,成就斐然,并且影响到当代印坛对陶瓷印的热情探索。请问您最早是怎样接触并喜欢上陶瓷印的?
王丹(以下简称王):这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,我那时工作在铁路文化宫,当时有几位版画家在搞创作,我帮他们用油墨印制版画的同时就想:能否把篆刻刻大,用印版画的方法印制篆刻,那样一定会有大气象……(印过大,印泥是无法钤盖的)就寻来长城维修下来的大砖一试,刻了许多尺方的巨印,在几个大展中拿了大奖。这就是我在非石材上探索的开始。
砖也是陶,它的硬度松软,肌理苍茫,有砖的特有质感。刻时我是按刻小印的刀法,朱、白文皆双刀完成。双手握刀,从前往后拉、披、削,故不失刀法。在刻砖题跋中题云:“书有榜书,印有巨印,然,书可以拖布式巨笔翰之,壮伟如崩云、惊涛;而巨印多以石为之,大亦有限。余北地人也,喜以古砖治印,尚觉可吐胸中弘气。昔见有君刊砖多细细琢成,线条绵而不畅,余刻石印法铭砖,一气而成,自然流露,此道行者甚稀,丹当勇猛精进之。”
但砖刻虽大,而实用性欠缺,把砖切成小块,松软班驳则索然无味;若用陶土刻好再烧一定会好,但当时苦于找不到烧陶的地方。
1992年在日本留学期间,有缘完成了我的梦想。因为那时日本的陶瓷艺术教学已走进社区,我很快掌握了烧制陶瓷的技术和性能,便一发不可收。
谷:您认为陶瓷印与普通的石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我们看到,有的作者刻出的陶瓷印与石章无异,这一方面扩宽了陶瓷印的表现范围,但是另一方面,我们认为并没有表现出陶瓷印独特的审美价值。请问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。
王: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,它是陶瓷印价值体现的核心。无论什么材料都是以印章为载体(萝卜、肥皂都算),为什么叶腊石(寿山、青田、巴林)成为主体印材?一是易刻,二是漂亮(可把玩)。易刻受刀,使艺术家成为主体,可以使文人有无限的驰骋空间。故而到齐白石止,石材印章的质感到顶峰;快刀披削的精准流畅,韩天衡老师已到极致。
实物把玩时,材料越“名”、越“古”、越“兴奋”。欣赏印屏、印花时,有可能“萝卜”、“泥巴”盖出来的味道更过瘾、更新鲜、更轻松。故而印章创作是不拘泥材质、种类的,只要它适于表现(专指印屏创作)。因为印屏(印泥、墨拓)是载体,印材已是幕后了。说到这,我讲个故事:上世纪80年代,我刻砖,河北马丹青在玩古封泥了。他改名为古泥,他的“泥”和我的“砖”屡屡获奖。我驱车几百里去迁安讨教,他拿不出一件“泥”给我看,笑咪咪的不理我。最终酒后吐真言:“白文刻在石膏上,封泥打在橡皮泥上。”我问:“橡皮泥软怎么拓?”他随手从冰箱的冷冻室里拿出一块冒着冷气的“封泥”说:“这就硬了!你想让它变形,在冻之前用手扭曲一下就有味了……”事隔20多年,那些石膏、橡皮泥不知是否还存在,可是古泥的名字和那些鲜活的印迹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古泥用最简单的材料,抓住了“泥”的质感,结果出了精彩的印屏,在展览中夺冠,应归功于“泥”!
陶土做成坯,未烧之前,硬度要软于石,经800度烧制后与石同,在这种硬度上刻出石章意味甚至刻出元朱文是很容易的事情,因此可见陶瓷印材是极富可塑性的。反过来讲,用石料刻出砖文、封泥、陶文味道也是正常的事情吗?而陶瓷坯的“软”和种类繁多的“质”,易于创造的“钮”和五彩斑斓的“釉”,烧完之后的“变”最终达到的“硬”,把玩时的“韵”,更是让艺术家激动的事情,它是有别于石章的。“软”,可以自由自在,奇怪生焉;“质”,可产生不同的线质;“钮”,无硬度障碍的尽情发挥和边饰的无限创意;“釉”,四大名窑和民间作坊的釉彩任你装点;“变”,意外的惊喜,意料中的快乐,失败的遗憾……过程让我生活的充实、宁静且充满遐想。
艺术以创造、创新为宗旨,在石章上人们也在创新,在陶泥上更能有广阔的空间。特别是刀法的走向可上冲下拉,左拨右披,角度尖(锐)、钝、薄厚及其它工具等都可以尝试,最终符合印章的艺术规律,而不是无“陈”之“新”。在整体三维空间的把握上亦可有更多突破。
谷:能否介绍一下您创作陶瓷印的过程,我想这是读者特别是喜欢陶瓷印创作作者最感兴趣的地方。
王:我是认认真真在做这件事情的,我围绕“虎溪窑”的田园建设有13年了。开始是用原始的方法烧低温的陶印,把用陶坯刻好的印(陶土是当地的)放在地上,先用废纸,再用茅草,然后用树枝,最后架上粗木棒(如同联欢点篝火),就是让陶印一点点升温而不炸裂,就可以烧成陶印了,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。因为你在陶坯上的表现最终要烧结才能钤盖、把玩,故而窑是必须有的(如果没有可以借用),但要多少掌握一些陶瓷方面的技术。我现在已自建电窑、煤气窑,大小都有,拥有全国各地及国外的陶土、釉色。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。
把各种陶瓷泥(粗、细、白、红、黑)都制成大小各异的坯,自然干燥(我不用烧成800度、变石章硬度的方法,那样刻起来没有感觉)。根据你要刻的字数多少选坯,设计印稿时要严谨,刻时尽量使陶土的“泥性”表现出来,如何控制刀法的准确,就要反复实践来体会心得。之后做钮,因为软,简单的瓦钮、穿孔、边饰的创意,在无任何硬度障碍下很快就完成了。之后再选釉色,釉是泥浆状的,拿着印面把钮的部位浸入,几秒后拿出(紫砂印就不用上釉了)。再放入电窑或煤气窑烧就可以了。
天下陶瓷过程都一样,印面的韵味、风格体验是印人长期积累的感悟。陶印尚未游离出中国篆刻艺术,钮、釉做得再漂亮,印面不好,它也只是工艺品,而只有印好、钮好才是一件完美的“中国印”。
谷:您对当代陶瓷印创作的整体评价怎样,您认为其前景如何?
王:自前几年举办的首届陶瓷印展之后,全国陶瓷印创作呈现繁荣景象,在展览媒体上清晰地展现了陶瓷印的韵致,印人已经在对新材质的把握上找到感觉,我坚信随着陶瓷制作科学的普及,陶瓷印创作一定能有良好的前景,流派一定能够形成(这应该是后人总结的)。
谷:请谈谈在您的创作中,篆刻与篆书相互影响、相互促进的体验。
王:篆刻与篆书是“孪生兄弟”,先贤已给我们做了榜样。在篆刻创作过程中,如何体会篆书笔墨、线质的生命力,是一种感觉,特别是在设计印稿时的书写、选字、变易、挪让、增减,要有“己”意,上石(陶、瓷)更要强调“书写性”、刻时的“流畅性”。不管工稳、写意,如此做来都会有灵魂。
谷:现在的书坛,因为交流的便捷,地域书风渐渐淡化,就篆刻而言,工稳、写意作者全国到处都有,请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。您认为个人风格的形成中,发乎己性的成分多些,还是受地域、流派书风的影响大些?
王:书风的导向来自国展的获奖、入选作品。地域之风在20年前是很分明的,因为当时有地方“偶像”,而当下,学“偶像”不如学“传统”,学“传统”,不如学“获奖”。“入选才是硬道理”。篆刻也是一样,在展览上工稳、写意,只要作品好都可入展、获奖。过去的“江南娟秀”、“北方粗犷”的观念荡然无存。我认为是好事情,自古“印人”决不是单纯“印人”,今天“印人”就是“印人”,“印从书出,印外求印”是也。
谷:您在研习书法篆刻的同时还醉心绘事,请问您的学画经历怎样?您认为书画篆刻的共通性规律是什么?
王:我受益于绘画。
我自小学画,画的像不像就是模仿能力,书法、篆刻临的像不像当然也是模仿能力,绘画“天赋”让我受益无穷。我中学完成考美院的全部课程,又酷爱雕塑。因雕塑认识李世伟先生,我开始习书法、篆刻和制印钮。1980年我拜大康、韩天衡先生为师,他们是书画集于一身的艺术家。1985年我到浙江美院(今中国美院)进修,有缘在陆俨少先生身边生活了一年,成为入室弟子。三十年来,我一直在书、画、印三方面并行学习,从无懈怠。
书、画、印三者我认为都是形象思维,古云:“书画同源”。绘画,“形”是最基础的基础,书、印亦然,故叫“形神兼备”。形,代表“准确”、“结构”、“精微”;神,代表“韵味”、“质感”、“情绪”、“感觉”。前者是遵守客观规律,后者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。
谷:您与日本书法家有着密切的联系,而且您也到日本进行了长时间的艺术交流,请您介绍一下日本书坛的现状。
王:日本书法,是“老年书法”、“兴趣书法”、“师承书法”,虽然书法人口众多,以在日本几个有影响的展览为核心,开展各项活动,每年大同小异。大一点的“日展”、“读卖展”、“每日展”、“产经展”,中等的“独立展”、“连盟展”等等。从每年的1月10日一直到2月份,东京都美术馆整个展厅全是书法展,热闹非凡。围绕展览,各种小协会加盟大协会,就成了产业链。除了精神上的,其它是商业行为。
谷:据说在日本,老师要比传统对学生的影响更大,是这样吗?日本书家的生存状态怎样?
王:日本的书法教育是“私塾”教育,老师就是标准,老师给学生写的、刻的就是教材。不管多大年龄,有没有“天赋”都收为弟子,所以学生的“要求”不“高”,也很单纯,只是预防老年痴呆,身份大的书法家也收这样的学生。由于“无为、心静”,我看有的老人写字的境界不比老师差,学生也不自知。我唯一接触日本群马的一个以今成先生为首的书法家群体,以临摹中国古代经典碑帖为学习核心,临得像极了,可是一落款又一点也不象。我给他们讲课说“临创”关系,他们也直点头,之后还是那样。日本的书法家不好界定,人太多了,有的有家产,有的靠“私塾”。随着老一辈的人相继去世,带有人文意味的书法家、印人则越来越少。他们对中国书法的崇尚心态和认真精神实在令人钦佩,当然,学派之间“相轻”、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“劣根”在日本也确实存在。
